文章原标题:我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
十月的一天,阿关专程去了趟北京,在佑安医院的性病艾滋病门诊挂了个专家号。
他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山东读书,目前正在准备考研。
问诊的专家姓李。他看了看阿关填的基本信息,竟有些慌,「你是从青岛来的?」
阿关说「是」。他能理解医生的这种恐惧,毕竟,在他等待被叫号的时候,青岛新增病例数据还挂在新浪微博的热搜榜上。
2020 年,几乎人人都经历过这种恐惧。新冠疫情爆发初期,铺天盖地的新闻和流言使得人心惶惶,每个个体都陷入了对一种传染疾病的普遍性恐惧中。在恐惧中,任何微不足道的危险因子都被无限放大,而一个从「疫区」来的年轻人,更是会被看做可怕的活体传染源。
「恐惧」这种情绪,阿关很熟悉。在过去的数月中,他每时每刻都被浸泡在巨大的恐惧中,茶饭不思。
恐惧的对象很明确——他害怕自己被感染了艾滋病。
恐惧的缘由则并不明确——无论如何求证,他的每一张化验单上都明明白白地写着「阴性」。
阿关是一个典型的「恐艾症」患者,即「艾滋病恐惧症」患者。
这是一个庞大且痛苦的群体。虚幻的恐惧意念像真实存在的病毒一样折磨着他们,令他们惶惶不可终日。
万一我就是那 1% 呢? 阿关告诉李医生,他希望能在佑安医院做一次 HIV 抗体检测。 大约在三个月多前,他经历了一次无保护性行为,对方是邻校学长。这是阿关第一次对同性产生好感。 他本科读的是医学相关的专业,防范意识相对高一些,便特意从淘宝上买来了 HIV 试纸,在发生关系前,要求学长测一次。学长虽感到突兀,却还是顺了阿关的意,最终的检测结果也没什么问题。 但最终,他们也只是发生了一些边缘性行为。「说得直白一点,只是蹭了蹭,没进去。」 回到学校,不安的感觉再度袭来。他检索了一些相关研究,发现 HIV 试纸的检测准确率大约在 97% 到 99% 之间,一下子便慌了神。 「万一我就是那 1% 到 3% 呢?」 他给学长发了微信,要求他跟自己去一趟医院,再做一次检测。但这一次,学长似乎失去了耐心,骂他是「神经病」。 一条又一条的语音消息连番轰炸后,他发现自己被对方删除了好友。 阿关联想到那些真真假假的社会新闻,譬如「艾滋病感染者为报复社会,隐瞒病情,与多人发生性关系,而后一走了之」,便愈加慌张起来。 于是,他立即赶到医院,挂了性病科,做了抗体检测。 检测结果依然是阴性,而医生也认为,阿关的感染风险并不大。但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还是要求医生给自己开了艾滋病阻断药。 在此之前,阿关对阻断药,也就是常说的「后悔药」多少有些了解。他知道,在高危暴露后的 72 小时内服用这种药,可以有效防止病毒扩散;他也知道,这种药需要连续服用 28 天,停药后才能再去做检测。 但他想不到的是,服药的这 28 天竟成了他这辈子最漫长、最煎熬的 28 天。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干等,仿佛悬在虚空中。他无心复习,无心玩乐,置身炼狱,只能一篇又一篇地翻阅与艾滋病有关的文献,越读越慌。 更糟糕的是,他不敢向任何亲友吐露半个字。 他怕自己就此被当成瘟神,连手都没人敢握。他怕别人讥笑他「搞同性恋,活该染病」。他更害怕自己被当成是一个私生活淫乱的人,毕竟说到底,他也只是做了一次无关公序良俗的性尝试而已。他甚至担心,一旦消息散布开来,谣言四起,没准未来的学业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 某种意义上,他所恐惧的已经不再是艾滋病本身了,而是在长久的固有认知中,与艾滋病相关联的一切羞耻与罪恶。 终于,28 天的服药期结束了,他从虚空落回了地表。按照医嘱,他在停药的第 14 天和第 28 天都去做了复查,每次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但问题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的疑虑。越来越频繁的确认行为导致阿关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放在了是否患病,以及身体状态上,因而焦虑感反而越来越强烈。 而在强烈恐惧的同时,他也在经历着强烈的羞耻感。对于一个同时存在这两种心理感受的人来说,羞耻感也往往会阻碍他的有效行动,致使他无法用向外倾诉的方式去克服自己的恐惧感。 最终,无计可施的他从青岛去了北京,希望佑安医院的专家能给他一锤定音。 「你没事,你也不用测,」那位姓李的专家听完他的一通讲述,直截了当地下了这样一个判断。 但他似乎也见惯了像阿关这样的恐艾患者,几经央求之下,便安排了检测。 这次的检测结果依然是「阴性」。 脱恐与复恐的较量 从佑安医院回来后,阿关轻松了好多。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逃离了那种如影随形的恐惧。 对恐艾患者来说,这叫做「脱恐」。 但是第二天,他无意间发现,自己的右手上有一道细细的伤口,像是被划破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类似这样的传言:某艾滋病感染者在确诊后爆发了反社会倾向,将自己的血涂在针头上,在街头随机刺伤路人,传播病毒。 那道细小的划痕立刻勾起了阿关的联想。他想到,在佑安医院排队等号时,他曾隐隐约约听到走廊里的其他病人在聊复查和换药的事,看来八成都是确诊的艾滋病感染者。万一他们当中有新闻里说的反社会分子怎么办? 冷静下来后,他上网查了些资料,发现所谓的「艾滋病人用针头报复社会」其实是假新闻——艾滋病病毒一旦离开了人体的环境,很快就会丧失传播能力,即使针头上有病毒残留,病毒数量也很难达到致病条件。 但是,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阿关再次被与艾滋病有关的信息洪水给淹没了——比如有的帖子在猜疑艾滋病门诊的医生在给病人抽血时,有没有可能忘了换针头。 他无法自控地开始重新在记忆里检索,在去佑安医院检查的过程中,还有什么环节可能会出问题?万一医生真的没换针头怎么办?万一医生没换酒精棉球呢?万一检测的设备出故障了呢?万一医生恐同,想捉弄我,没做检测,直接在我的检测结果栏填了「阴性」怎么办? 某一天,阿关六神无主,在与母亲例行通电话时,忍不住试探性地提起了「艾滋病」这个话题。母亲立刻起了疑心,质问他是不是「在学校里交了不三不四的朋友」。他慌忙搪塞过去,陷入了莫名的负罪感和羞耻感。 就这样,阿关「复恐」了。 他不堪其扰,卸载了微博、知乎、谷歌搜索等一切检索信息的 App,并取关了所有的健康类公众号。 但他忘了,大数据的算法已经牢牢记住了那些他常常搜索的关键词。于是,每当他好不容易喘口气,靠动漫或是游戏把自己从恐艾的世界里拉出几分钟时,一条关于「艾滋病」的推送就会神出鬼没般地显示在他的屏幕上,将他再次拉入深渊。 阿关说,他非常恐惧 12 月的到来,因为 12 月 1 日是他的生日,同时也是「世界艾滋病日」。 他决定,到了那一天,他要关闭手机,隔绝从四面八方袭来的那些与艾滋病有关的消息,同时,也将错失所有来自朋友与家人的生日祝福。 「恐艾」是病,要治 事实上,每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对恐艾患者来说,都是一道坎。 张珂做了十多年的恐艾干预咨询老师。在他的印象中,每年的 12 月,都是咨询的高峰期。 张珂所在的成都市恐艾干预心理网是国内最早,也是唯一的专业从事恐艾干预与预防治疗的机构,成立于 2009 年。 在张珂的经验中,他所接触的恐艾患者大多数是大学生,或是商务人士。 「事实上,很多恐艾症患者对艾滋病核心知识掌握的正确率高达 90% 以上。但问题是,关于艾滋病的一些医学观点和说辞都没有得到完全统一,毕竟人体存在着个体差异,而这些差异也不能全部靠实验去得出结论。而这与恐友们的期待是不同的,他们想要的是完全确定的安全信号,因此,基于群体得出的医学观点反而会加强他们的恐艾情绪。」 而在张珂接触的「恐友」中,存在着大量多次脱恐,又多次复恐的案例。在漫长的折磨中,很多「恐友」的恐惧都泛化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比方说,他曾接触过一位有着十多年恐艾经历的「恐友」。在病情最严重的阶段,他甚至恐惧空气能传播艾滋病毒,因而将自己锁在家中,窗户密封,还备有两台空气净化器。 而他最近刚开始接触的「恐友」老金则是将他的恐惧延伸到了亲人的身上——他时时刻刻都在恐惧,自己的儿子长大后会不会「学坏」,从而感染上艾滋病。 老金的恐艾是从 19 年前开始的。那一年,老金在大学里第一次接触到了艾滋病相关的科普,联想到自己曾经跟朋友一起光顾过一次风月场所,便陷入了恐慌。 但在漫长的十几年间,他一次又一次的复恐已经和最初的那次「高危行为」没有关系了。每隔三个月,他都要瞒着家人,偷偷去做抗体检测,情绪则伴随着每一次的检测进入死循环。 大约两年前,经过长期的自我调节,老金本已经渐渐「脱恐」了。但就在那一年,一个近在咫尺的噩耗击溃了他——他听说,家里的一位远房亲戚确诊了艾滋病。 关于那位亲戚是如何染病的,老金没有打听到确切的说法。消息一出,多数亲友都与那一家人断绝了来往。只是在闲谈时,聊起这回事,多数人都猜测,那位十有八九是沾染了什么不光彩的习气,不值得同情。 老金就这样再次复恐了。 这一次的复恐比以往更加严重。他甚至向妻子编造了借口,带着儿子去做了一次艾滋病抗体检测,以暂时平息心中的不安。毕竟,摆在眼前的是活生生的例子。老金无法承受,自己或是自己的家人沦落到和那位亲戚一般的下场。 最终,他找到了成都市恐艾干预心理网,希望能通过干预摆脱无休止的痛苦。 通常来说,恐艾干预心理咨询师会通过情绪和行为习惯的评估和干预来对患者进行调节,常用的疗法包括森田疗法,接纳承诺疗法和精神分析相关的”方法。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老金则刚刚踏上第一步。 为什么是艾滋病? 人人都会恐惧,但并不是人人都会成为恐艾患者。 仅以张珂自身的咨询经验而言,他所接待的恐艾患者 90% 为男性,20%~30% 为性少数人群。而如果要谈论更具客观性的群体特征,还要从「恐艾」形成的心理机制说起。 对恐艾患者而言,他们之所以会陷入这种心理困局,首先,在他的身上必然发生过一个作为刺激源的「高危行为」,例如无保护性行为,或者工作过程中有密切接触感染源的机会;其次,在已形成初步恐艾的基础上,大量不确定信息或者谣言的摄入会导致患者的恐惧发生「泛化」;此外,多数恐艾患者本身存在相似的心理特征,例如天生敏感、容易焦虑、不擅消化压力和痛苦。 某种意义上,这与「疑病症」的发生机制是类似的。张珂认为,对于疑病症的人群来说,恐艾的表现出来的痛苦反应会更大,濒死感会更强一些。 一方面,这关系到艾滋病本身的致死性,以及传染途径的隐蔽性;而与此同时,关于艾滋病群体的负向信息和污名化,也成为恐惧的重要来源。 由于艾滋病常常被与一些负向信息,比如吸毒、性乱,以及性少数群体联系在一起,很多恐艾患者在恐惧病毒之余,也恐于向亲友倾诉,从而进一步加深痛苦。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些负向的隐喻在关于艾滋病的相关叙事中被日渐强化,互联网的信息传播速度又扩大了影响的范围。与艾滋病有关联的个体们,在信息的偏差、印证与传播中被塑造成了身负病毒,行为不端,有着道德污点,甚至反社会人格的「罪人」。 于是,通过影视、标语、新闻报道和网络上的流言,这些负面典型,成了阿关母亲口中「不三不四」的朋友,成了阿关臆想中那些走廊里的艾滋病人手里藏匿的带血的针头,成了老金的亲戚们对一位血脉相连的病人的污名化想象。 而与之相对,不仅是艾滋病患者,恐艾群体也在遭遇着同等语境下的污名化。如果他们无法走出被污名化的恐惧,正如老金一样,一个微小的契机就足以把他们拉回恐惧的深井里。 做了十年恐艾咨询,张珂自己偶尔也会产生应激反应。比方说,去医院采血的时候,他时不时也会冒出「针头换没换」的念头,甚至会在自己的梦境里看见某个「恐友」描述的可怕景象。 张珂觉得,像这样的恐惧很正常。而事实上,过去的几十年里,正是对疾病的恐惧帮助人类更有效地传播了与艾滋病防治有关的基本常识,从而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但面对艾滋病,人类所能给出的反应也许不只是恐惧。 作为群体而言,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艾滋病的抗争。而作为个体,我们可以试着去尊重,去体谅,而非下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事外,从而将与艾滋病有关联的人群区隔为「他者」,区隔为与自己无关的「劣等群体」。 恐惧基于自我保护和求生欲,而区隔则基于污名化的联想。这些联想对于人类与病毒的抗争无益,只会对那些因恐惧而陷入病理性困局的人造成二次伤害。 他们不一定是「完美受害者」,但他们值得获得一个出口,去逃离无因的恐惧。 (阿关和老金皆为化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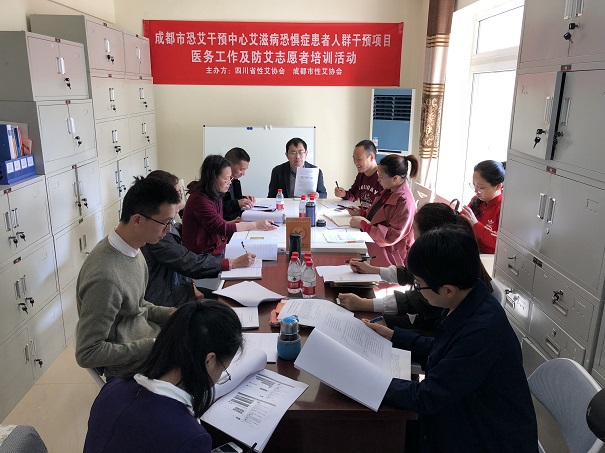


 会员登录
会员登录






 点击进入
点击进入
 QQ客服
QQ客服 返回首页
返回首页